谈写《信念》的背景与经验
——在广州首届世界华文文学大会上的发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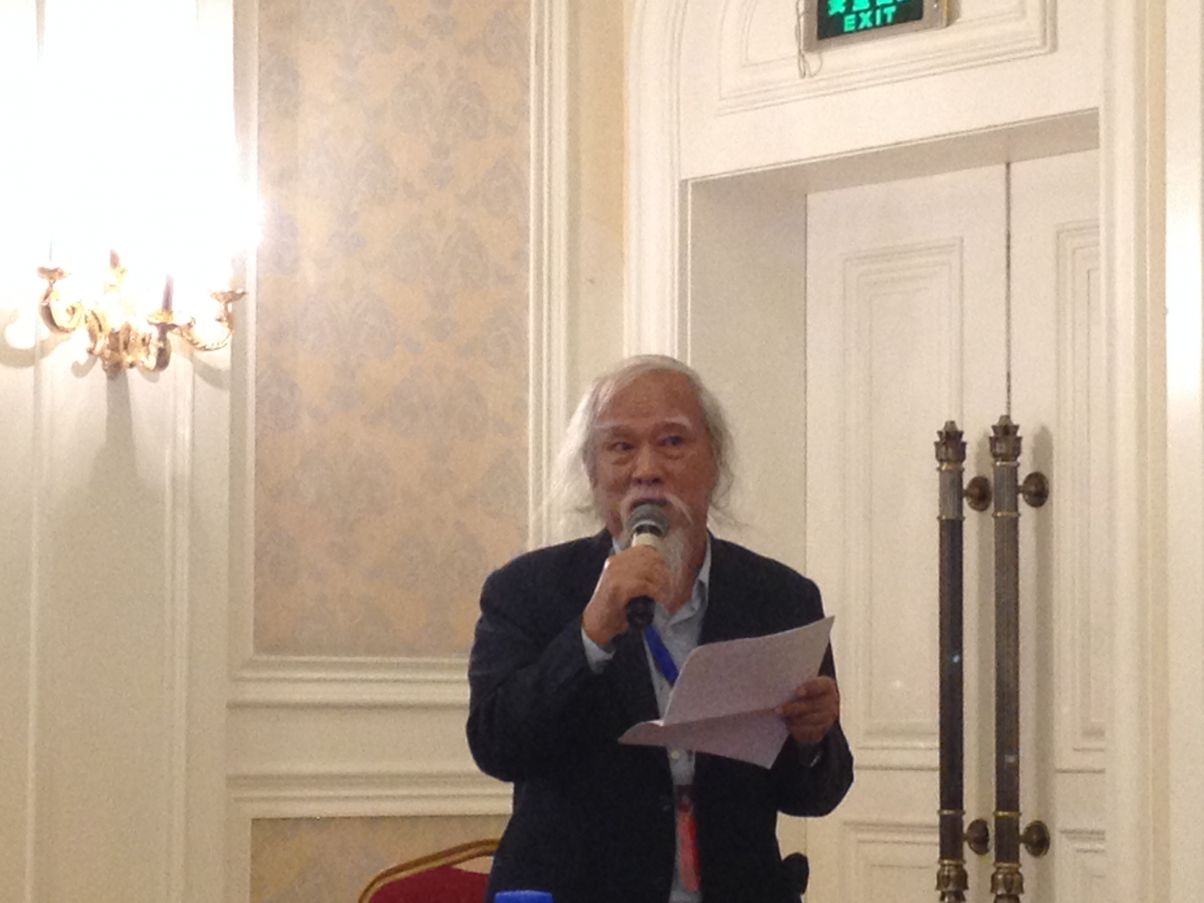
“经典诗歌对话论坛“规定要作者谈谈创作的背景与经验,我以为一篇作品的创作背景,似乎应由旁人来说更恰当,由作者来说,不免主观。我对诗学没有什么研究,这里只能漫谈一点关于写《信念——观秦俑有感》的时代背景和亲身经历,讲得不好,请各位评家指教。
他们焚我以烈焰
坑我以沙石
而我不死
我等待
等待一万年後
重见天日
这一天终於到来
我听见掘井的铲声
我听见人语
我兴奋地挪动身体
而我的躯已折
骨已碎
蓦然
一抹强光
伴着人间的惊呼
照见我
残损的微笑
——《信念——观秦俑有感》
《信念》一诗是我于1986年5月29日访西安观看出土的秦俑后,有感而作的。诗发表后,引起一些反响,特别是在中国,受到评家的赏识,那是我始料未及的事。
1986年5月,我生平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那时期马来西亚政府尚未开放民间对中国的访问,但作为马来西亚经济访华代表团的成员,我有机会后随团到中国各地,而身为一位赤道歌者,我有幸游览游华夏风光景物,沿途写了系列诗作,如《长安赋》、《旅者》及《信念—观秦俑有感》等篇。
我生长在南洋,在婆罗洲 ,就是现在称为东马来西亚一州的砂拉越。我的祖父在清光绪年间即来到那里,我已是第三代了。我生于1937年,经历过英国人拉者王朝统治、日本帝国主义统治、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争取独立运动,到今天马来西亚国的几个历史时代。我的父亲在日本统治时期曾经坐牢,我在参与争取砂拉越独立斗争中,于1966年与妻子被捕入狱,一同在集中营中度过10年的时光。我入狱时29岁,出狱诗已39岁,失去的正是我们最宝贵的青春岁月。
我的两位兄长也坐牢,一个还长达十五年。而于此同时,我的许多老同学好朋友都在斗争中牺牲了。
是的,我们离开监狱那一刻,实在有一种重见天日的感觉。
但不论经历如何,在自己看来,写诗似乎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一种如佛家所谓的活在当下的体验,如古人的所谓触景生情表达。我曾说过,我把文学创作当作是自己生命的延续,它的内容即是生命的感知,它的形式即是感知时自然的形态。因此,所谓创作,是一种出自于自然的生命表达,它无需予制造,它是一种自我的实现。
当见到出土的秦俑时,看到他们残损的身躯,想到他们在黑暗的地下度过千年,那蓦然出现的一抹强光,令我很震撼。他们的面容坚定如故,他们没有死,他们靠着生存的信念终于重见天日。
追究起来,我的生活背景也许就是的我写《信念》的背景吧。
我坐牢的十年,也正是中国文革的十年。我出狱的时候,也正是文革结束的时候。到中国,我也有一种中国人重见天日的感觉,特别是对中国的老一辈的知识分子,感染到他们劫后重生的喜悦。
回想起来,在我初到中国时,在写观兵马俑一诗之前后几天,也写过类似残损的微笑的意象。
5月23日,在前往天津的京津火车上,我看见一位满脸皱纹的老人,我写了《皱 纹》一诗:
“我看见他脸上/深深的皱纹/当他笑的时候/
在那一季烈火的/烙印下/有风的笞痕/雪的啮迹/
龟裂的河床底/半个世纪的风砂/湮没了/青春的酒涡/眸中的浪漫/
但我依然窥见他的笑/在他深深的/皱纹里”
5月23日,在桂林游漓江时,我写了《阳朔感怀》一诗:
“此刻/我的心/是你无痕的水/平静是折腾后的一种/澄澈/正如一切微笑/流自悲泣/纵有你/ 嶙峋奇突的倒影//它曾经洪荒/曾经崩裂/曾经溶岩与狂涛与/此后一万万年的风雪的洗礼/修成碧莲朵朵”
或许,这也是一种如当时中国文坛的所谓“伤痕文学”吧。
我说《信念》一诗引起的反响,是我始料未及的。第二年,1987年,我在新加坡一间豪华旅店的咖啡厅里,遇见一位来自北京的年轻女记者,她笑容可掬,明丽照人,她翻阅着我赠予的诗集,当她读到那首描写秦俑的诗,忽然俯在诗页里,泣不成声……我于是写了《在我的诗上哭泣吧》一诗:
“是重见天日的喜悦/在等待一万年后的今天/是挪动残肢的痛楚/当听见人间的呼唤/当时我只知道/残损的微笑/是死亡的解冻/现在才知道/哭泣/才是生命的重燃/哭泣吧朋友/在我的诗上哭泣/我的眼睛也润湿了/你我/已复活在万年后的/天涯海角……
2014年11月8日凌晨 于古晋葛园

 seacpw.com
seacpw.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