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壇的賽車手和指揮家
--我與余光中接觸的幾種方式
/白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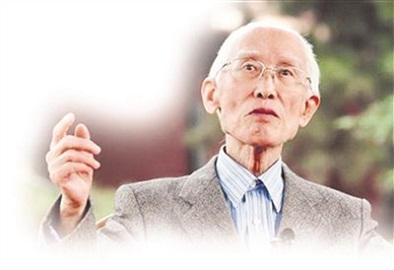
一
从少年起就有剪报的习惯,读高中时的1960年代每天最爱做的,就是先买一份那时最红最大的中央日报,留下副刊那张,然后其他的就丢到垃圾桶。那年代很穷,爱读副刊上中外各式作家的小说和散文读到迷,就很希望报纸只卖副刊,那就不用饿肚子,还可省下一点钱去旧书摊买书。那几年中央日报或联合报、中国时报副刊上最常出现的作家,就是余光中了。
年少时代的两大册剪报现在还留在手边,他的诗我只剪贴了一首,他的散文却剪了至少七,八篇。剪的那首诗叫《天使病的患者》(1967年9月24日中央日报),16岁还未接触过新诗的我在剪报旁边用钢笔对此诗作了批评:“余先生,咱们这傻瓜呆头呆脑,只知这是篇小文外,再也读不出什么诗的意味,即使读了五遍。”这竟是我对余先生这篇有讽刺调侃意味作品的最初印象。而在隔年12月中国时报上他的散文《食花的怪客》剪报旁则写:“这是一篇别有象征的文章。他的文章很不错,用字不特别斟酌,清新自然,文句简实而兼具幽默,具有诗人洒脱自然的气韵。”读他的诗与散文竟有这么大差距的反应。
这样对新诗不佳的印象到了18岁的日记里依然没有改善,还写说:“报上有一篇访问余光中(按:他约40岁)谈关于灰色书刊的界说,谈得还不错。……大家都知他是出了名的诗人……但我对现代诗根本没啥心得……好像幼稚得很,就那么简单的意思却啰嗦了老半天……还有另一派诗人难懂难理解,总觉得很浅薄。”如此一直到十九、二十岁,因喜欢余先生的散文而买了他的《逍遥游》《掌上雨》《左手的缪思》《望乡的牧神》等散文集,这才发现每本集子内抒情散文并不多,议论式的最多,且还大半是讨论诗的。这才开始耐下心来,看他到底为何这么衷情于诗。
读每本集子讨论诗的还一篇篇作了笔记,比如关于《望乡的牧神》的笔记最前面我写道:“24篇文章中属自传式抒情散文只有《咦呵西部》《南太甚》《登楼赋》《望乡的牧神》《地图》五篇,篇篇精彩,真是把散文艺术化了。其他篇章多是有关文学尤其是诗的批评。”如此,我对现代诗(新诗)的认识竟是从他的散文集中大量关于诗的介绍剖析、中西诗学观念的文章开始的。而由于从1950年代直到1960年代末台湾仍处在一片西化、现代化乃至崇洋的声浪中,我开始喜欢新诗并非读台湾诗人的诗,而是读了华裔菲籍翻译家施颖洲译的《世界名诗选译》《古典名诗选译》及余光中译的《英美现代诗选》(1968)开始的,当然读的最多的是翻译小说和存在主义,光西洋小说大部头的在20岁以前就读了一百多本,散文读最多翻到烂的就是余光中的了,“中”新诗的“毒”即由此开始,散文竟像是他传播新诗的障眼法、魔术道具了。
二
等到1975年杨弦首度在台北中山堂举行演唱会,将余光中《白玉苦瓜》诗集中《乡愁四韵》《民歌》《江湖上》《乡愁》《民歌手》《白霏霏》《摇摇民谣》《小小天问》等八首诗谱成民歌,掀起长达18年的校园民歌风潮。而众所皆知,此民歌诗体的开始,是青年期的余光中去美国多次,深受比他年轻的鲍勃·迪伦的影响,由余氏《江湖上》与鲍勃《随风而逝》(Blowing in the wind) 的极度相似性即可知。此后台湾各式民歌纷纷出笼。包括席慕蓉、郑愁予的诗也被谱成曲,又有别于通俗流行歌曲和深奥的艺术歌曲,民歌等于当了两者桥梁。从此民歌手更是多如过河之鲫,影响迄今,这两年还办了“民歌40”,接着“民歌42”,可见其深入民间有多深。
余光中诗歌前后被谱成曲的至少有35首,居台湾诗人之冠,歌比诗更易入肌浃髓,其影响之深远非纯粹的诗文字所能比拟。也因这些一天到晚透过电视广播乃至校园学生演唱他的歌诗作品,令人不能不抬头乃至侧耳想办法听得仔细明白些。
当然,在这之前,他的《白玉苦瓜》(1974)已是他中年创作的高峰,超越之前《天使病的患者》甚远。后来再追索才知他与新月派诗风的关联,尤其1950年代豆腐干体、形式整齐还押了韵脚的诗形,但后来转学闻一多《奇迹》一诗长达49行不分段、一气呵成的诗形,贯穿了余氏后来的不少诗作。西方留学经验、译诗经验、以及深受东方古典诗的熏陶,使得他在1960、1970年代有极大的转折与混杂。如同1950、1960年代其他的台湾诗人一样,那时他对现代与西方充满了幻想和遐思, 并于其中挣扎。在《白玉苦瓜》之前的诸诗集名称中,古典与现代名词交叉出现即可见出这些痕迹,比如 “天国”的夜市﹑“万圣节”“天狼星”“敲打乐”等西方名词的中间或前后夹杂了“舟子”的悲歌﹑“五陵少年”“莲的联想”“紫荆赋”“隔水观音”等东方想象的名词。而对东方古典的想象就如同他被迫逸离的大陆原乡, 于后半生也成了他所倚靠和凝望的另一个远方。西方不能久待,遥远的东方(指大陆)不能回去也不能触及,“两个远方”成了1949年所有大陆来台诗人在1950、1960年代最重要的符码和象征。而余光中在他诗中展现上述“两个远方”的两极性的纠葛和对抗,大概是台湾诗人中最显著的。而民歌诗体学自西方,内容寻索东方,像是两个远方的一种和解或握手。
三
我与余光中第一次有机会接触的地点是位于台北罗斯福路与辛亥路的耕莘文教院,他在此演讲、授课,都是有关于诗的,留下了许多青年余光中的身影。耕莘文教院是1960年代西方文化、自由民主观念进入台湾最重要的窗口,也是台湾异议分子发表言论的舞台,一直到1980年代它在台湾文化史上都扮演关键角色,实验小剧场、诗的多媒体化(今日叫跨领域或跨界)都由此开端。此处离台大、师大才几步路,而余光中曾是台大的学生、师大的老师。
耕莘文教院是1963年由天主教耶稣会的一群神父创立,那时台大外文系有一半的教授都是这里的神父。1966年美籍神父张志宏因小说家王文兴的建言创办了“耕莘暑期写作班”,授课一个月,内容全是有关现代文学的,教授皆是一时之选,余光中是其一。此写作班与由救国团(蒋经国创办)每年举办的“复兴文艺营”是那年代最重要的现代文学作家培育基地,今日中年以上的台湾作家至少一半都参加过。我因是学理工的关系,很少机会认识心仪的作家、找到同好,1973年参加了复兴文艺营,营主任是亚弦,因此认识了洛夫、商禽等诗人。1975年加入耕莘,从学员成为辅导员、指导老师、班主任、理事长,现在是志工,一待就超过了40年,却仍然是一个佛教徒,在那里也跟耶稣会神父学会了付出不求反馈、与人分享美与文学就是快乐的精神。
一直到1978年,我才有机会与余光中接触,那时我名义上是耕莘暑期写作班的班主任,却才27岁,刚出道,作家没认识几个,即被指派担重任。余光中也不认识我,我只能与他略略寒暄几句,但从此与他有了联络的方式和管道。那一两年正是台湾乡土文学运动炒得火热激烈之时,“大乡土”与“小乡土”等现实主义作家因为理念的不同,相争互扛,余光中一篇《狼来了》,搅翻一缸水,从此对余氏的声誉造成不小损伤。余那时正在香港教书,一待11年(1974—1985),写了163首诗。
等到他由港回台,前往南部的高雄就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我与他的接触才频繁起来。他大概是台湾诗人群中最常坐飞机在岛屿的上空“高来高去”的一位了,仿佛从台北派遣出去的“文化巡抚”,自愿发放到文化边缘地区, 与那些笃实朴直的人群为伍, 一字一句在他们耳边诵念文化经典,比如1986年他就发表新诗《控诉一支烟囱》,对高雄的空污语多讥剌,之后却也为高雄市木棉花文艺季写诗《让春天从高雄出发》,甚具鼓舞作用。即使住高雄,他因常跑台北,有时也接受我的邀请到耕莘来演讲,记得那次讲题是《诗与音乐》,口才便给,风趣幽默,朗诵起自己的诗或英诗,叮当铿锵,真是一场享受。
四
有一天他找我去他厦门街巷弄中的家搬书,说要送给耕莘。那条与尔雅、洪范等出版社同一条巷子,一楼屋内很多东西已搬走,书房中书架高高大大一整排,三分之二已搬走,剩下的三分之一余先生说都送耕莘。我费了好大劲才搬回耕莘,大部分交耕莘二楼图书馆,小部份藏耕莘写作会,如今图书馆已撤,书早散四方去了。有一年他在中山大学办文艺营,找我及张大春、陈幸蕙去当驻营导师,参观了他的院长办公室和住家,均布置整齐、舒适宁心,怪不得他愿远离台北,待在高雄,不过那时高雄的水质真不敢领教,人人都只喝矿泉水。
1989年九歌出版社请他当中华现代文学大系(1970-1989)总编辑,诗卷二册主编为张默,我与向阳为编辑委员,等到2003年再编大系贰(1989-2003) 时,他仍是总编辑,我则是诗卷主编,与他又有数度接触。其能言善道,机智优雅,坐必端正、行必挺胸,数十年始终如故。
很少有哪一位诗人的诗会像余光中的诗那样贴近他的生活, 或者说, 很难得有哪个诗人的生活会像余光中的生活一样, 那样地贴近诗, 他是极少数能与英美文学﹑诗教学厮磨一辈子的诗人。他诗中与自然﹑人﹑历史﹑文化的互动成分, 要大于其他同代诗人悲苦﹑自嘲﹑自残﹑孤寂的成分, 形构起的自我与他者因此也较完整, 这与同时代诗人遂有了分隔和差异, 恐怕也是他诗作能源源不绝的原因之一。探究其中根源,或许与他是前行代诗人中少数于1949年后与父母同行来台有关, 其余大多为只身来台的年轻军人和流亡学生。台湾“偏安七子”(包括洛夫﹑余光中﹑周梦蝶﹑痖弦﹑商禽﹑郑愁予﹑杨牧等人)中军人即有四位。 杨牧生于台湾花莲, 余光中与郑愁予均以流亡学生身分来台, 由于有父母同行, 此后他们两位乡愁的内容与情感的孤绝度, 即与四位军人身分来台者有极大的不同, 他们人生的障碍和要克服障碍的方式, 也有显著差异。表现在余﹑郑两人的诗中的, 温馨成分要远大于悲绝成分, 尤其余光中十岁以前在江南母亲娘家的情感记忆, 两度逃难过程眼睛所见﹑身体所触﹑跟母亲长期相依逃亡的体验等等,皆建构了他诗中想象物不同于其他诗人的内容。
余氏有十一年住香港, 后三十余年住高雄,他仙逝之前还在海峡两岸之间每年十来趟飞来飞去, 表现了异于常人的活力与生机,他曾有句名言,说:如果不做诗人,他最想当的是赛车手和指挥家,赛车手是玩命的职业,指挥家要熟悉各种乐器的本能和天分,更要有照观全局的本领,在在都得具有极大的企图心,他像诗坛的牧师或祭司,要把诗的奥妙、文学的天机传达予世人。即使到临去,他依然创作不懈, 这样的毅力、动能和行径,或值得后辈学习、参酌。

 seacpw.com
seacpw.com